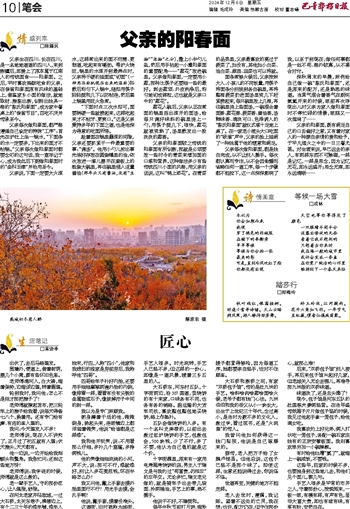□陈耀民
父亲生在四川、长在四川,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四川人,来到新疆后,却爱上了原本属于江南人的传统面食——阳春面。之后,平时喜欢捣鼓吃食的父亲,在保留阳春面原有风味的基础上,借鉴家乡小面的做法,就地取材、推陈出新,创制出独具一格的“陈氏阳春面”,成为家中餐桌上的“保留节目”,百吃不厌并传承至今。
父亲每次做阳春面,都严格遵循自己设定的特殊“工序”:首先在炉灶上坐一锅水,“下面条的水一定要多,下出来的面才不粘锅。”父亲每次做阳春面时都要念叨的这句话,我一直牢记于心,成为我此后下厨做阳春面时的“金科玉律”并沿用至今。
父亲说,下面一定要大火滚水,这样煮出来的面不烂糊、更筋道,吃起来有嚼劲。等炉火烧旺,锅里的水滚开到最沸点时,父亲将干硬的挂面或“切面”(一种用压面机现压出来的湿面)抖散后均匀下入锅中,随即用筷子轻轻搅和几下以防粘连,然后盖上锅盖用旺火急煮。
“下面时点三次水即可,面要稍硬一些就捞起来,这样吃起来才不粘牙、更爽口。”这是父亲秉持多年的下面之道,也是他深为得意的吃面所悟。
趁着面在锅里翻滚的间隙,父亲还要抓紧干一件最重要的事:“调汤”。他用小勺儿挖出事先炼好存放在圆瓷罐里的油,依次放进一溜儿摆开在案板上的粗瓷大碗里,再往碗里倒入适量酱油(那年头只有酱油,没有“生抽”“老抽”之分),撒上小半勺儿盐,然后用手拈起一小撮阳春面的重要配角——“葱花”放进碗里。父亲做阳春面,一定要用小葱,那种比筷子还要细一些的最好。剥去葱须、外皮洗净后,均匀地切成碎粒,这也就是父亲口中的“葱花”。
葱花入碗后,父亲从正在煮面的锅里舀出滚开的面汤,给每只调好味料的碗里浇上一勺,用筷子搅几下,很快,葱花就被烫熟了,汤里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葱香。
父亲的阳春面较之传统的阳春面有所创新,那就是必须要放一些时令的青菜来增加面的口感和营养,这种做法多少有些传统四川小面的风格,用父亲的话说,这叫“锦上添花”。在青菜的品类里,父亲最喜欢的莫过于菠菜了,如没有,其他如小白菜、油白菜、蒜苗、韭菜也可以将就。
面条煮够火候后,父亲按照大人、小孩儿的不同饭量,用筷子将面条分别挑到各自碗里,再将整根菠菜扔进面汤里烫几下赶紧捞起来,每只碗里放上几根,再往碗里浇上些面汤,一碗混合着面香、葱花香、菠菜香、酱油香,汤鲜味香、清淡可口、色泽诱人的“陈氏阳春面”就仪式感十足地上桌了。在一家老小埋头大口吃面的“吸溜”声中,父亲的脸上挂满了一种独属于他的惬意和满足。
父亲每次做阳春面,都是独自完成,从不让别人插手。每次都认真而专注,从不会因偷懒而省略任何一道工序,每一个步骤都不能拉下,这一点深深影响了我,以至于到现在,做任何事都是一丝不苟、格外较真,从不凑合对付。
深秋周末的早晨,照例给自己做一碗“陈氏阳春面”,还是原来的配方,还是熟悉的味道。当蒸气混合着香气在厨间氤氲开来的时候,眼前再次浮现出儿时父亲为家人做阳春面时不停忙碌的情景,眼眶又一次湿润了……
父亲的阳春面,既有满足自己的口舌偏好之意,又有着对家人的一种源自亲情的爱和给予,于平凡烟火之中的一日三餐尤甚。对生者来说,早已远去的亲人,有两样东西不可触碰,一样是记忆,一样是思念,因为记忆无花,却永远盛开;思念无痕,却永远清晰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