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尚新革
1956年3月1日,父亲配戴大红花,在铿锵的锣鼓声中光荣地参军入伍,成为哈尔滨某部一名战士。
1957年8月末,哈尔滨发生特大洪水。8月28日,黑龙江省军区派出解放军支援抗洪抢险。
当天,父亲连夜上堤。岸边堆的全是防洪物资,他站在没膝深的泥水里,光着脚,背着百十斤重的沙袋一路小跑。抢卸完一车石头或是装满湿土、沙子的麻袋和草包之后,他的手上、肩上、背上均磨破了一层层皮,勒出了一道道血痕。然而父亲对此不管不顾,依然拼命地搬运着各种抗洪物资。麻袋供应不足,大家就把宾馆、招待所的被罩、床单、窗帘撕开,缝制成口袋装土;抗洪物资供应不及,加工厂就拉来装满面粉的袋子顶上……只要能用的都用上了,试图阻止洪水对大堤的侵蚀。但这些办法都无济于事,汹涌的水浪扫过之后,堆积如山的物资便不见了踪影。
父亲与突击队员用铁丝捆扎石头“滚石堵口”,用草包填土封堵渗水处,用打桩机夯实大坝的泥土,用草席铺在大堤上护河坝。他们还在大坝外侧,捆扎了一组又一组防浪木排,以减弱风浪冲击大坝的势头。累了、困了,就睡在坚硬的石堆上、满是泥巴的沙袋上、潮湿的堤坝旁,甚至是战友的肩头……
9月6日,松花江哈尔滨段的水位达到120余米,更为危险的是,哈尔滨在松花江持续高水位的20天里下了9场大雨,甚至刮起了7级大风。松花江沿岸的顾乡、太平、马家船口等处,出现366次脱坝、管涌等险情,江水高出临江街道一米多。
狂风暴雨一起袭来,雨点打在脸上就像被鞭子抽打一样疼。父亲与战友们全身都湿透了,在冷风中直打哆嗦。此时,河堤出现一处决口,排长大喊:“二排战士,跟我上!堵住决口!”战友们纷纷响应,有的搬起大石头憋气扎猛子,在深水中堵漏洞;有的被水底的石头划破了手脚,却不顾伤痛,抢时间争主动。
因为水势凶猛、管涌不断,刚扔下的石头马上就被冲跑了。汹涌的江水还在不停地上涨。有人提议:用人体拦住水流,再用石头填。然而,第一批战士刚刚跳入江中,就立刻被湍急的洪水冲散。
“二班长,用绳子把战士们拴牢!挨着下!”排长冒雨指挥着。
父亲与战友们腰间连着绳索,相继跳进奔腾的江水,手挽手组成一道人墙,才不至于被冲散。哈尔滨的九月,人们都已经开始穿大衣御寒了,父亲却只穿了单衣,即使被冰凉的洪水冻得脸色青紫,他也不肯让别人替换。他只有一个想法:严防死守,保住哈尔滨!
三天后,父亲的身体严重透支,下肢失去知觉,皮肤浸泡得发白,并布满褶皱。他因身体变得浮肿,浑身直冒冷汗,头、手不停地颤抖,被连夜送往哈尔滨医院救治,从此落下病根,“抖抖病”伴随了他的一生。
9月20日,滔滔松花江水终于被驯服——哈尔滨保住了!全市人民以抗洪胜利的姿态喜迎国庆。
10月1日,为纪念全市人民战胜特大洪水,哈尔滨市在中央大街北端建起一座防洪纪念塔。松花江水映衬着这座雄伟的防洪纪念塔,这座塔不仅是哈尔滨一处亮丽的风景,更是哈尔滨作为英雄城市的象征。
2024年年初,我来到哈尔滨。当我静静地站在防洪纪念塔下,心情与所有旅游打卡者不同,因为这座纪念塔凝聚着父亲的血与汗。
如今,父亲早已离我们而去,但那句“严防死守,保住哈尔滨”的铿锵誓言,仿佛仍在耳畔回荡。
面对防洪纪念塔,我双手合十,深情地三鞠躬,为父亲,也为当年所有的抗洪战士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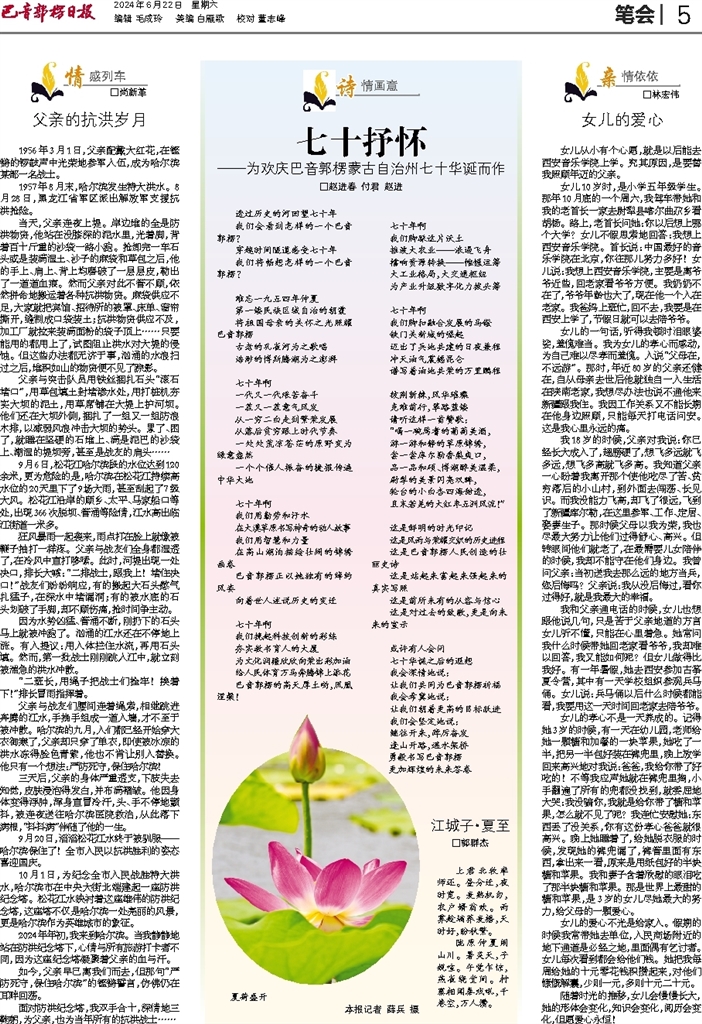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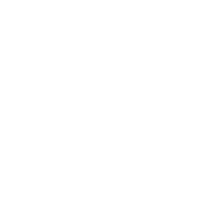
 放大
放大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