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解家忠
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山东农村度过的。来到新疆已经快五十年了,每逢过年,我就会想起小时候在老家过年的情形。尽管那时候人们都不富裕,物质非常匮乏,但在过年上还是很重视、颇有仪式感的。
赶年集。那时年前最高兴的是跟大人去赶集买年货。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“炮市”,就是卖炮仗的地方。在一个宽阔的场地里,停满了大大小小已卸了马的马车。车上装着各式各样的炮仗和烟花。卖主们一边声嘶力竭地叫卖,一边点燃用长竹竿挑起的一串串鞭炮,或者手提几个大麻雷子,点燃,顿时响起一阵剧烈的“噼里啪啦”炮仗的爆炸声,引得围观人群一阵叫好,纷纷涌到其车前购买。此处炮声刚落,又有一商贩扯着嗓子喊起来,接着又是一通响亮的炮仗声。整个上午,商贩的叫卖声,炮仗燃爆的“乒乒乓乓”声此起彼伏,烟雾缭绕,热闹非凡,既有浓浓的年味,也让本来就热闹喧嚣的集市平添了几分喜庆。
出豆腐。每到快过年时,母亲都要亲自出两锅豆腐。豆腐作为廉价而好吃的食品,平时都是从走街串巷的小贩处用豆子换来的。只有到了春节,家家户户才会自己做豆腐吃。先把黄豆放进水里浸泡一夜,让豆子全都膨胀起来。然后,用自家院子里的石磨磨成豆浆。在搅拌均匀的豆浆中倒入滚烫的开水,大约半小时后,再把豆浆倒入棉纱布过滤,将豆浆和豆渣分离开来,把豆浆放进大锅中烧开,倒入用石膏制作的发酵卤水,也叫“点卤水”。很快屋里便弥漫出豆腐的香味。此时,母亲会给每人舀一碗豆腐脑。最后,母亲把凝固了的豆腐脑倒入一个铺上过滤用的白纱布的方形木框内,包好,再压上一块石头,定型,豆腐就算做好了。
现在想起那时自己也曾参与过的豆腐制作,想起烟火气和豆腐香气氤氲的厨房,想起母亲忙碌的身影在蒸汽中若隐若现,那番景象仿佛就在昨日那般令人难以忘怀。
穿新衣。过年能穿新衣裳是儿时的我盼望过年的缘由之一。春节前夕,母亲都会忙着给我们几个孩子做新衣裳。那时父亲在新疆工作(七级锻工),每月都会寄回来50元,但勤劳、节俭的母亲,基本上不用花什么钱,就能让我们过年“一身新”。鞋底是母亲一针一线纳的,鞋帮是母亲用旧布和浆糊粘的,只有鞋面一般都是用买来的黑条绒布做。而新衣服新裤子,也是母亲用亲手纺的线织的布,用缝纫机缝制而成的。到除夕晚上,我们就迫不及待地穿上一身新衣裳,口袋里揣一些拆散的炮仗,和小伙伴一块儿跑到外面去放。
走亲戚。大年初二以后我们开始走亲戚。过年走亲戚,是中国人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习俗,是一种亲戚间联络感情、互相慰问的活动。很多不是特别近的亲戚一年到头也不联系,更谈不上见面,所以能够维系亲戚关系的事情,就是过年时的相互走动。母亲要在家中接待来拜年的亲戚,走不开,于是小小的我就承担起了替大人“走亲戚”的使命。那时走亲戚是真正的“走”,没有任何交通工具,全靠两条腿步行。母亲通常会给我准备好装了馍馍或者嵌有红枣的花卷、饼干点心之类的包袱或竹篮,一连几天走好几家亲戚。
走亲戚最大的好处就是:在亲戚家会受到热情接待,能吃到好饭好菜。回来时,亲戚不会把所有礼物留下,一般会回赠些礼品。我记忆最深的,是去一个嫁到旭升大队山庄村叫“玲子”的远房堂姐家,她年龄比我母亲略大一些。我每次去给她拜年时,她都特别高兴,同时用带着感伤的语调对我说:“你可别到新疆去啊,你走了,我就没有娘家人了。”
斗转星移,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。随着岁月的流逝,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,更少了采购年货、做年食的忙碌,而年味却越来越淡。尽管儿时厨房里的烟火气、身穿的粗布衣、炮市的鞭炮声、亲戚的叮咛声等等早已远去,但那种特有的年味至今仍萦绕在心怀,久久不曾淡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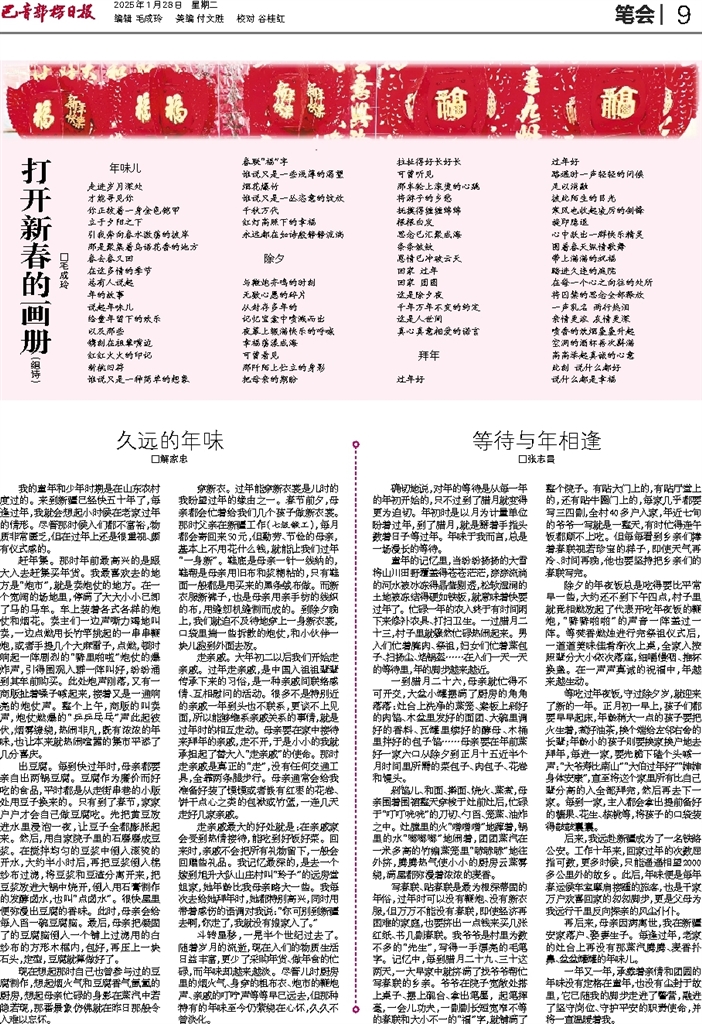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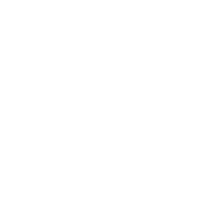
 放大
放大

